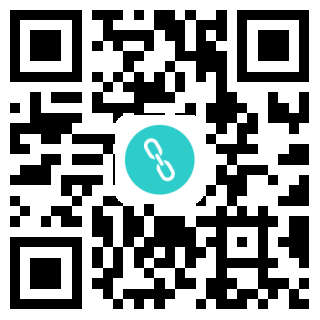翻译与品味
品味是一种无形的判断力,如翻译般游走于多样与不确定之中,引领我们感知善与美。
学会拥有品味,其实就像学会翻译。
翻译让人明白,世界上从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。一个词句,可以化身多种译文,每种都合理,却没有一种能彻底还原原文的神韵。它们或许捕捉了意义,却失落了节奏;保留了意象,却削弱了暗示。正是这无可避免的缺憾,提醒我们:所谓“好”,从不是单一的绝对,而是繁复的、多声部的。翻译因而成为一种训练,教会我们在差异和不确定中去辨识“善”的存在。
然而,翻译并非完全遵循规则,它像是一种冒险:自由而不可预期,成果时常悬而未决。它与穿衣打扮、布置空间、筹划宴席相似——稍有不慎便显拙劣,但若恰到好处,便能令人心悦诚服。能把握这种微妙的,不是教条,而是品味。
品味,既是个人的能力,又是事物的特质。有时它近乎某种神秘的启示,仿佛美与善自带光芒,不容置疑;有时,它却只是私人的好恶,“这本小说不合我口味”——一个轻巧的句子,既无理据,却自带分量。而在另一些时刻,品味又能跨越个体,汇成群体间的共鸣:人们在电影、音乐或美酒面前相视一笑,仿佛心灵短暂地达成和声。
在哲学家Hannah Arendt看来,品味与判断之间有着深刻联系。她强调,判断是一种独立的心智实践,不同于冷峻的思考,也不同于果决的意志。通过康德的重读,她指出:在人类缺乏规则和权威时,审美的交流——凭借说服与共鸣而非逻辑与律令——或许是我们感知世界“善”的途径。
这种感知不是宏大的道德体系,而更接近日常的细腻体察。它是一种对他人感受的敏锐触碰,一种在差异中寻找和声的能力。Arendt担忧,现代社会太容易放弃这种注意力,人们被舆论、宣传和陈词滥调牵着走,却少有余裕练习独立的判断。
在她未竟的遗稿中,翻译与品味常常相互交织。她的弟子Michael Denneny甚至追溯“taste”一词,指出它自17世纪以来,既是身体的愉悦,又是美学与伦理的桥梁。那时的思想家们更偏爱格言与对话,而非冰冷的理论,他们用灵巧的文字展示如何以品味化解孤立的思考与僵硬的规则。
耶稣会学者Dominique Bouhours曾写下“je ne sais quoi”——“某种说不清的魅力”。它存在,却难以命名;它触动我们,却超越逻辑。这样的概念,并不是对理性的逃避,而是一种更轻盈、更接近生活的理性。
Bouhours在《如何在文学中正确思考》里,让两位绅士反复辩论哪位作家更优。他们以翻译为工具,互相修正、互相感染。这样的场景,不只是文人的雅趣,更是伦理和政治智慧的缩影:在差异之中,透过不断转译和共鸣,磨炼出一种可以共享的品味。
Denneny最后说,品味的世界是科学无法精确描绘的,却也不同于主观任性。它是一种“常识”的领域,是人类在缺乏规则时仍能找到的真实依托。翻译与品味因此成了穿越时间与文化的桥梁,让我们在模糊与多义之中,依旧能捕捉善与美的光辉。